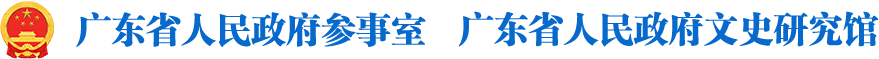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导致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反复执行“禁海”,以实现其“片板不得入海,一贼不得登岸”的愚昧政策?
在宋代及之前,中国的海洋是敞开的,汉武帝派出的第一支朝廷的船队,是由黄门译长所主持的,黄门,即近待,是皇帝最亲近的供应部门,一般由宦官担任,相当于皇帝的内务部门,大内总管之类,可见重视。这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史以来由文献记载下来的第一支船队。到了唐代,更有“广州通海道”。五代年间,南汉国的皇帝,相传有海上的血统,故对海上贸易情有独钟,不仅南方的所有口岸是开放的,皇帝还亲自设宴款待来自中东、南亚各方的海商,鼓励海上贸易,以致南汉国被视为“金玉帝国”,连离宫都以千百计,宫殿的宝顶均是金铸的,而下边的沟渠则用珍珠所铺就,其兴王府外的离宫备极奢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三城之地,成为离宫苑囿”,人称岭南园林则于此起步,融皇家园林与商家园林于一体。
及至宋代,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宋神宗,一直力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在北方用兵失败,可在南方用商则是成功的,使东西、江南迅速富裕了起来,其中一条,他认为南汉国最为成功的经验,便在于“笼海商得法”,于是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争而阻塞,所以愈加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营,广州首设市舶司,而后又设杭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在其治理间,广州的市舶司一直称雄天东南各口岸。虽说仍没有跳出朝贡体制,但市舶司制度的完善,尤其是规定贡品以外的货物,须一律在广州交易,这也使互市更为发达了,宋代沿袭唐代、南汉的传统,每年都由市舶司的官员,专门宴请外商,以表示友好并鼓励加以贸易。
所谓“唐强宋富”,与海上贸易是分不开的。
加上南方大兴水利,稻谷激增,宋代人口也突破了1亿,是唐代的一倍还多。广东,即当时的广南东路最为富裕,各市舶司中,“唯广最盛”。外国商人一晚是大量聚居于广州,且可以在广州添置产业,与当地人通婚,甚至可以改为汉姓,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建筑形制,都不受干预。
然而,当元后南下,把宋代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带往西方之际,却在中国实行了严酷的海禁政策。
元代一共实施了五次以上的海禁。
这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每每在海上受挫,往东多次征伐东瀛,却屡遇台风,折戟而归;往南也一样,在南洋一再败绩;往西,打到里海,也就弑羽而归,于是,对大海产生了天然的恐惧。到了明代,更是反复地禁海。郑和下西洋,我同意不少学者的分析,它其实就是海禁政策的产物,本已网开一面的互市,重返了官方垄断的贡舶贸易,从而杜绝了民间的对外互市,当如朱明皇帝所称“商税者,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把外商说成是“慕义而来”,一说到——便“亏辱大体”,有损帝国颜面了,这是怎样的思维方式?
帝国的海禁,终于逼良为娼。所以后人有云,开海,则海盗变成海商,禁海,则海商逼为海盗了。严酷的海禁,令中国海上的巨商,不是破产,便是远走他乡。弘治十三年(1500年)凡是建造双桅以上的帆船者,即可处死——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前后。嘉靖四年(1525年),明王朝销毁了所有的海舶,通缉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食古不化的浙江巡抚朱纨竟一次处死了所有96位出海的船夫,他自命为清官却最终“以死明志”。
……于是,元明以降,别说官员亲自出面宴请外国海商了,连在广州居住,也不可能。官员更不得直接与外商接触,否则乌纱帽不保。只能通过中介即“牙商”方可以间接打交道,否则动辄得究。到了清朝,由于郑成功海上的“金厦帝国”一度严重威胁到清皇朝的存亡,空前的海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惨痛一页。笔者在长篇纪实《宝安百年》中,已详细描绘了海禁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实在是不忍再加以引述了。下边,仅列举清廷禁海的时间表。顺治四年(1647年),也就是清立国后仅三年,便在广东实行海禁,不允许中国海商出海贸易,只允许外国“贡使”(其实,人家大都是有海商相随),“悉从正道,直达京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更进一步向沿海各省颁布了禁海令。
翌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明确禁止浙、闽、粤及江南、山东、天津等地“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贸易,也就是扩大到几乎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上。而广东,凡是“无号票引及私制二桅以上大船”的出海贸易,更全部禁止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则因为郑成功屡次从海上支援南方的义军,为了切断海上与陆上反清代队伍的联系,更发布了“迁海令”,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25千米,其范围从山东一直到广东,一场人间浩劫就此发生。其内迁25千米,为的是“以绝接济台湾之患”,害怕郑成功卷土重来。一时间,近万里海疆,不仅渔船断绝,农田荒芜,民生凋敝,人烟渺无,饿饽塞道……康熙元年(1662年),限期三日迁界,“尽夷其地,穿其人”。
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朝廷又以“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再度下令,往内续迁15千米,加上之前的25千米,一共为40千米,以致本非濒海的县份也被划在了里面,如广东的顺德、番禺、南海、海阳。一如《广东新语》所言,“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这一迁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老百姓被迫弃儿卖女,“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拏投河……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之,而民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这里说的“粤东”,不同于今日的粤东,指的是广东东部,而是整个的广东,解读不一样了。如今日的吴川算是粤西了,但当日亦在粤东之意义内,其“人民十死八九”、遂溪县“仅存粮六百石”之地,新安新界“迁移之民,十存二三”。新会则“仅存一半……”
官逼民反,番禺市桥疍民周玉、李荣起兵反清,扬帆出海,发动起义。而后,惠州碣石卫总兵苏利也发动了抗迁起义。海南汉、黎民亦一同起义。
虽然起义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伤亡数以万计,但也宣示了濒海百姓对迁海的反抗。“迁界”之暴政,延续达数十年之外,生灵涂炭,而“复界”后,禁海仍在继续。照旧民不聊生。
“复界”,是在众多地方官员的呼吁之下,且直接影响到了清王朝赋税收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地方名士胡日乾就上书广东巡抚王来任,上书中字字看来皆是血:鸠形鹄面,尽是富豪之家;鼠啸燐青,半作含冤之鬼。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及至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已在病危中的王来任遗疏请求朝廷“复界”:
臣思设兵原以捍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寇侵掠,虑百姓而资盗粮,不见安壤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臣抚粤二年有余,亦未闻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内地被迁之民,相聚为盗。今若展其疆界,即他盗亦卖刀买犊耳。
这才为已掌权的康熙谕允,是年11月,朝廷派大员会同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周有德等巡视,“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第二年二月,终允许广东在康熙三年的迁界区复界,也就是仅恢复后来继续内迁的15千米,而沿海已内迁的25千米还是禁区。故复界后新界跃头乡仍记载有:
流亡八载,饥死过半,界之复也,复田而不复海。新安偏邑,鱼盐为利,海界不复,渡海不通,究竟同归于尽云尔。“复田不复海”,这复界意义何在?
纵然“迁海令”造成沿海人间惨剧,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奄奄一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州这个千年商都与世界大港的入口与出口贸易,并不曾完全禁绝。海外贸易也仍有非法与合法的两类途经。
澳门本已让葡萄牙人“租居”,明清易朝,顺治四年(1647年),两广总督佟养甲疏请“通商裕国”,“仍照故明崇祯十三年禁其入省(即进入广州)理贡舶贸易与非对外朝贡贸易。
康熙元年迁界后,澳门自然被免迁,却划在界外,“内地商民禁止不许至粤”,澳门也就没了生意,直到康熙十八年才为朝廷允许于广东和澳门“旱路贸易”。
康熙二年,荷国助剿海逆,并清贸易,奏旨著二年贸易一次。三年定,凡外国进贡,顺带货物,贡使愿自出夫力,带来京城贸易者听,如欲在彼处贸易,该替抚委员监视,勿使滋扰。五年奉旨,荷兰国既准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
这一来,葡萄牙人做不成生意,荷兰人也没戏了,八年一贡等于不做。
不过,私下里,当广东还为藩王主政,康熙十三年(1647年),尚可喜亦不顾朝廷的管束,当苏禄国王森列柏遗使三人来广州请受藩封时,尚可喜仍大模大样颁给驼纽银印,付以时完,“一时称荣”。这一来,南洋诸国贡使便成群结队来到广州,“夷利”为之大开。
而澳门就近的十字门,则一直成为广东等地商人的大规模走私的据点,未曾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