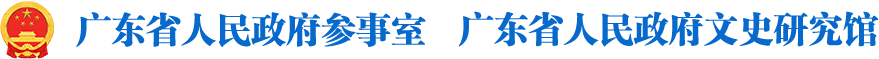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几年后,康熙二十三年,即在台湾收复之后一年的一月份,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的进士杜臻,由京城派往广东,以钦差的身份,宣布开豁迁海之禁,还民以地,使民复兴。他还特地与另一些大员吴兴祚等去巡视了一番澳门,对澳门兴旺的贸易艳羡,为此,特写下一首七言诗《香山澳》:
香山之南路险巇,层峦叠嶂号熊罴。 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 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 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竣宇开通衢。 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 金碧荧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蛟螭。 风琴自鸣天籁发,歌声呜呜弹朱丝。 白头老人发垂耳,娇童彩袖拂冰肌。 红花满座延上客,青鸟衔桃杯玻璃。 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温咿。 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 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 我闻此言甚欣喜,揽辔停骖重慰之。 如今宇内歌清晏,男耕妇织相熙熙。 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 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祀作藩篱。

康熙皇帝
后边十行,与其说是用以慰藉澳门的“白头老人”,不如说是让北京朝廷的“圣人”看,以证明葡萄牙人“归顺”后,如何“坚守臣节”的,故圣上无须为此忧虑。
诗中对海上贸易的盛况描写,当为不虚,因为从外国的典籍上,也同样可看出澳门葡人是如何赚得盆满钵满的。
当我们涉足这一历史时期之际,无论资料的多寡,都是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进一步深入下去,甚至会对既往已形成的定见,或者某些历史的结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我们当看到的,是与过去已在头脑中产生的图景完全不同的一幕,似乎混乱却又鲜活,似乎困厄却又自由。
如前所述,在康熙决定解除海禁的前几年,即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法国君主,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由于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地理并绘制航海地图,则已在酝酿如何与中国皇帝联系的事了,正是康熙宣布开海贸易的同一年,即1685年,“太阳王”终于派出了第一个科学传教团上中国,这个使团正是由日后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神父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所组成,他们都“入乡随俗”,起了个中国名字。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带着“太阳王”授予的测量仪器于布雷斯特出发,两年后,他们先抵达宁波,再过半年,奉康熙之命,到了北京,其中,张诚、白晋就留在了康熙身边,成了康熙的老师。
可以说,康熙在东方,也同样具有“太阳王”的辉煌。他与路易十四一样,都是冲龄即位,而且,全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智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走向了鼎盛——这边是康熙盛世,那边,则成为欧洲的强国,欧洲的科技文化中心。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清初中期,中国与法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法国甚至比英国早在澳门设立了贸易办事处,当然,法国的神父兼科学家、技工、画匠,也一直占首位,上边提到的张诚,还参与了中俄划界的谈判,甚至代表中国出使俄罗斯。
而康熙,一直努力在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技术,也包括人文学科,如哲学等,他完全接受了“地圆说”——这在前边已提及了,他接受科学,但对传教则始终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离京返回法国,给“太阳王”带去了康熙的礼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与科学著作(共49卷)。很快,不少著作被译成了法文,有的,成了反对神学,推动启蒙的思想武器。
正如法国当代学者所说:“在18世纪,大家实际上是目击了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主要是欧洲向中国学习。”“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法“太阳王”路易十四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写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
而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对法国如伏尔泰等大思想家,亦不无影响。笔者在同时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开洋——国门十三行》中,就专门写了一位醉心于“开明君主制”的十三行的法国商办主任。
平心而论,此时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而对外开放的态势,也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忽略这些,认为此刻的中国便已经僵化、保守,井蛙观天,实在与事实相去太远。
本来,通向世界的这一历史之门,已然洞开了。
因此,这里,我们选择了康熙开海之后的70多年——被大多数史学家们忽略了的历史。
在法国人认可的“开明君主制”下,中国这70多年的一步步开放,当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诸多关于开海、免税以及与十三行相关的御批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而言。
同样,在大清各级官吏中,为民请命,拼死要求开放海禁、洋禁,以及免除各种缴送、税项的,亦不乏其人。他们关心民疾,视国计民生为己任,加上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的主导,出于公心,敢于犯颜直谏,令人感奋。
尤其应突出的是,走在开海贸易前列的十三行行商,早期,他们自然褪不去官商的色彩,但随着与国际商贸相衔接,加上国家政策的相应调整,他们已很快向民商,向自由商人靠拢,而且,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对外贸易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才一步一步褪去朝贡的色彩,最后形成真正的通市,即市场经济……

法国传教士进呈给康熙皇帝的《亚细亚洲图》
仅这么简单点上几句,就已经很明白了,在这70多年间,中国曾面临多少的机遇,有可能与正在逐渐成熟的国际贸易的准则相适应,有可能更多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不再忧虑“岭门开后少坚城”,有可能在梯度的开放中,接受西方迅速发生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思潮——行商中已不乏这类先见者,有可能清中晚期不至于发生逆转,走向腐败与衰亡。当然,历史没有这么多的“可能”与“假如”,已发生的一切均已无法改变了的。
那么,这70多年中,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机遇?同样,行商或者相关官员有过怎样的抗争?而其间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为何在一路畅行之际,突然进入了另一扇门,令已进行得相当到位的开放最后发生了逆转?
这些问题,哪怕在今天,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之际,一般是那么振聋发聩——与这70多年相比,我们的开放时间刚好过一半,而我们尚须进一步开放的内容,还很多、很多,不仅仅到加入WTO为止。因此,选择这70多年来进行深度的研究,对今天而言,有着更现实更重大的意义。
我们当有更明白,更直接的历史之镜。
在那70多年中,于中央层面而言,似乎也有两条历史的逻辑线。
一条是从康熙开海,接受法国科学使团、制造热武器为开端,而后则是雍正废除了南洋禁航令,雷霆出击,严惩了中外不法商人与官员的勾结、破坏正常的罪行,及至到了乾隆,便是废除加一征收,取消缴送,给予外贸优惠政策,乃至设法完善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大海关的制度与政策——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大清中期,其开放的格局也就得以完成,尤其是边关热武器的使用与提高,也就没了日后让英军几千条枪打得国不成国的样子。
而另一条,则是康熙开海后,晚年被地方官员忽悠,又颁布了“南洋禁航令”从宽容到“禁教”并祸延到科学技术之引进,而后,便是雍正开洋后,却默许广东巡抚杨文乾再度祭起朝贡制度的“加一征收”以对付日趋繁盛的西方商船的到来,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一口通商”和《防夷五条》——日趋严厉的对外限制,终于在其中晚年,令整个大清帝国由盛转衰……我不知道,是否曾有人做过以上的梳理?至于官员,有力促康熙开海贸易的,也有以种种借口延宕乃至反对开海的;有向雍正申明“禁洋”之弊端的,也有于海关设立种种巧立名目繁多税种的,当然,更有在乾隆“一口通商”决定中发挥极其恶劣作用的——这其间,杨宗仁之于康熙,杨文乾之于雍正,杨应琚之于乾隆,这杨家三代人对广东封疆大吏的承袭,所造成的恶果恐怕难以三言两语说得清了。
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落在十三行行商头上。毋庸置疑,商人、第三阶级等等,在那样一个时代,均具有革命性的因素,这已不用我们多加阐释了。十三行行商,这批经营大规模的外贸业的历史骄子,在世界那样一个大航海时代,秉承传统的“通商裕国”的理念,求新求变,求与国际市场交融在一起,且带来了全球先进的文化思想,其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关于开海的御批
而在十三行中,从早期的藩商、王商,及督商、将军商人,渐渐演变为有相对独立身份,乃至独立人格的具有自由商人色彩的民商,可以说有一个相当艰巨的蜕变过程,毕竟,他们是封建大一统的制度下生存、经商的,不能不受到种种的制约。而这演变过程,恰好就在这70多年当中,尤其是中期,那些坚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仅敢于与官商勾结者抗争更敢于告“洋状”,揭发外商的不法行为的行商,该担多大的风险,有的倾家荡产,籍没流放,有的,甚至几度入狱。然而,正是他们的抗争与牺牲,表现出一种可以面对那个时代与环境之超前的思想,为后来十三行行商成为真正的民商扫清了庭院,为他们摆脱或屏蔽掉官府,让整个世界去经营其商业、金融业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应当说,对于行商的整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另一条历史的逻辑走向——还原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商,他们只能向前,义无反顾地向前,哪怕十三行毁灭了,也仍在坚持其作为具备近现代商人、实业家的身份与原则,为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廓清了道路。
因此,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行商身上,是不二之选。正是他们,创造了机遇,抓住了机遇,在无论怎么艰难劂绝的时刻,矢志不移,走着自己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十三行的灵魂所在。
抓住这70多年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化,我们当有更多的发现与感悟!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