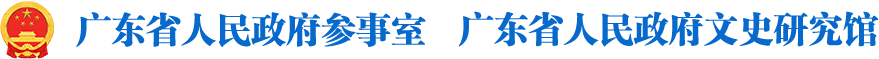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三、中国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可以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平衡。因为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无疑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
农耕经济时期,我国社会已萌发了环保意识。这种认知是直观和粗浅的,主要立足于生物圈、食物链认知的观察和思考。殷商之际已有严惩弃灰于道的官方规定,因为石矿粉、草木灰“令马落驹”或引发火灾。秦简《田律》禁止早春至7月前不得伐木、捕捉幼兽和毒杀鱼鳖。周代设有虞衡官职管理山林草泽,“衡”有平衡之意,《左传》载有“虞人之箴”劝诫包括帝王在内的狩猎者“德守不扰”。智者们更作了宏观的探索,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佛学中贯穿的众生平等、敬畏生命、善待他物等理念积淀成为各具特色的丰富生态智慧,共同期望则是一致的,即人、社会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的关系。
近代西方国家有关环保和生态问题的研究,约可上溯到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叶以来则有更多成果问世,大抵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视角,形式多样化——甚至采取了文艺的形式。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在1866年首先提出生态学的概念,当时还只是生物学的分支学科,至今已经形成了系列理念——相互联系原理、多效应原理和无干扰原理,“三大定律”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的认识深化过程。许多论著揭示了生态危机,确认已经构成威胁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公害,例如伦敦雾给人体带来严重的损伤,杀虫剂DDT的广泛施用造成了“寂静的春天”等等。19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生态伦理学,尝试从哲理的层面探究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了生态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上开创了“自觉”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鲜明地肯定存在对思维、物质对精神的本原性和第一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毫不含糊地肯定自然对人的本原性和制约性,同时也阐发了人与自然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自身连同自己的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史一开始就与自然史交织在一起,“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然而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人的意识、精神,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其最切近的来源,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人类创造历史的任何活动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人的意识、精神只有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成为物质力量,只有反映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我们统摄自然界,决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志得意满、为所欲为,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漠不关心、泰然处之,恰恰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摄,是在于我们比地球上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为之奋斗的人类解放,是在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中实现的,这两类矛盾的解决是同一个过程,是扬弃人的社会异化和生态异化,实现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伟大变革的过程。我们不懈追求的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它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和解,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和解。这种共产主义,将是 “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观、历史观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内涵,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和根本方向,提出了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