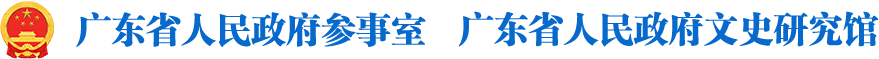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以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是人的自由的起点,也是人的自由的落脚点。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不仅是生产实践的问题,也是全部社会生活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唯物和辩证的方面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更多地从社会历史的方面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创了生态认识论的新境界,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实践中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造就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特性。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因此,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2]在既矛盾又统一的意义上,“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是在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中实现的,这两类矛盾的解决是同一个过程,是扬弃人的异化实现社会伟大变革的过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摒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实质上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深刻思考,是唯物史观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概括,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和根本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伟大理想。
在人和自然与人和人的两对矛盾中,人和人的矛盾起着主导的地位作用。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和条件,然而人之成为人,成为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是由于社会性的劳动实践,人的类属性即社会属性统摄人的自然属性。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4]人的这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本质在生产劳动中生成和发展,全面的生产劳动造就了人的全面的社会本质,而且要在实践中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进行生产,而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5]
在这里,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指出人不是被动的、直观的实现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是在实践劳动中达到对象化的、能动的统一。他也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劳动对象化、异化理论,黑格尔认为人通过劳动扬弃了自然界的原始性、异己性,使自己的本质统慑自然对象,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然而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精神形式的自我转换,而真正连接自然界和人类的是客观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不仅在于对象化,创造一个属人的自然界,而且在于非对象化,在自我否定中确证和发挥主体力量,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和潜在能力,只有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才能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者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详尽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首先,异化劳动造成劳动者与其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和外在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其次,异化劳动造成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的劳动是被迫的、痛苦的行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7]再次,异化劳动造成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把体现自己社会性、能动性的类本质的劳动本身变成单纯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使劳动者个体与人的类本质相对立。强制性、摧残性的劳动,使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觉得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劳动的机能变成仅仅维持吃、喝、性行为等动物的机能,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与个体的动物本能相对立。即使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提高了人改造自然能力,但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也成为了压抑人的自由个性的手段,“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最后,异化劳动造成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劳动者之所以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对象、劳动活动、劳动本质相异化,是因为他的劳动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下的劳动,“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9]马克思通过抽丝剥茧地深入剖析异化劳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中看到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中看到阶级关系,从阶级关系中看到社会形态关系,以异化劳动为钥匙,辩证地把自然观与历史观连接起来,打开了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奥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
消灭异化劳动是消除个体与类的对立的起点。异化劳动产生了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把一切人的劳动、分配、交换、消费联成一个整体,把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结成一个世界体系,然而异化劳动使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使私有主与无产者相对立,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限的自然承载力、社会消费力的矛盾,从而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产力的浪费,私有制与劳动社会化的矛盾在大生产条件下尖锐冲突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再也容纳不了社会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异化劳动必然要被联合劳动所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
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是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在蒙昧时代和封建时代,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明确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1]为了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论。人们对自然界的这种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关系又反过来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结合起来考察,提出了人类社会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三个阶段或形态:在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2]。异化劳动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它提高了每一个体的历史主动性,但“又在历史领域中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就是说,异化劳动一方面推动人的关系、需求、能力的普遍性发展,一方面又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和辩证性。当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再也容纳不了在其自身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时候,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被人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终于统一起来,人将“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3]。
马克思始终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根本标志,而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发展物质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基础条件,只有“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才能发展“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过是人类解放和自由的新起点,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处在为物质生产而奋斗的“必然王国”的历史阶段之中,以人的能力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是人类解放的神圣使命,而“自由王国”的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必然和自由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4]
(原载卢瑞华主编《中国生态哲学》,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出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集»第1卷,第81--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