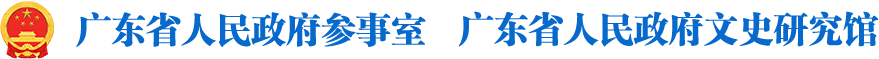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阶段,那么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最初的城市是随着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出现的,奴隶制时代,无论东方或西方都开始建造城市,但城市化却是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而兴起的。当前的全球化运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劲地推动着城市化的步伐,著名的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和城市计划设计者Lewis Mumford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说过:“从前,城市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象征;今天,世界自身正在变成一个城市”。①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化逐步以一种独特的性质和形态发展起来,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与时俱增,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以至今天许多文化流派都是围绕城市文化的批判与构建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大众文化、社区文化、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等文化样式到文化异化、文化霸权、文化冲突等文化话语,无不是从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内在矛盾中派生出来的。我国正处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城市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选择。
城市文化的产生以及它对乡村文化的胜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飞跃。斯宾格勒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②他还说:“城市是才智。大城市是‘自由的’才智。”③斯宾格勒对城市文化、城市文明的评价是复杂的,有许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但他看到了城市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现代城市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工业革命通过资本和市场,无情地撕破了以土地为依托的乡村的人身依附关系、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把人口、财富、权力吸纳到城市中来,城市不仅成为经济、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文化中心。相对于乡村文化,城市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胜利相适应,城市文化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文化,它打破一切陈规倡导创新,它摧毁一切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走向世界,它不断变化甚至每天都在变化,为工业化运动提供智力和价值的支持;与人的平等关系取代人的等级关系相适应,城市文化是张扬人的自由个性的文化,人的能力在职业的多样性、流动性状态中获得提升和发挥的广阔空间,人的价值也从神的光环和封建主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为万物的尺度。人的最高价值在于人的自身,文艺复兴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始终是城市文化的灵魂;与科学对神学的胜利相适应,城市文化是理性精神充分发展并主导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人类用头立地的时代即用理性而不是用臆想统治世界的时代。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也使人类深信科学技术的力量,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与平民对君主的胜利,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胜利相适应,城市文化是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文化。如果说,政治民主宣布了普罗大众的文化享有权的合理性,那么市场则是文化走出高墙深宫回归普罗大众的驱动器。教育、传媒、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不仅是劳动者再生产的需要,而且是资本增值的需要,不仅是市民宣泄的需要,而且是社会控制的需要。总之,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人类的精神生产如同大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化、全球化的生产,它把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召唤出来,把人的精神从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城市以不断涌现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文化巨匠,不断增加的大学、大剧院、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不断伸延的建筑群、大广场、交通网等文化象征,开辟了一个文化飞跃发展的全新时代,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充分肯定城市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是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工业化、城市化,就是用人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的方法去评价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马克思指出,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的书本。他的实践观、异化观以及世界历史的理论,为我们全面地理解城市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辩证方法。
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农业从属于工业,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力量和交往前提,然而推动着工业和城市在全球扩展的是资本和市场,资本和市场的统治又造成了人的本性、人的关系和人的社会的异化。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运动席卷全球,城市越来越广泛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城市文化的异化特征日益显现出来。城市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它造成了现代人的“物化”。资本的本质是增值,无限扩大的生产必须由无限的消费来充当动力和引擎,现代城市由生产的中心转变成消费的中心。从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百货商店、商业广场到20世纪盛行的商品交易会、主题乐园,从冰箱、汽车、音响设备等享受型消费到名牌、狂欢、礼品等炫耀型消费,奔涌不息的商品洪流主导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文化价值,正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引起了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④城市文化通过各种媒体、广告、交易会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为获得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为获得表明步入上流社会的商品而展开的斗争,使得新商品的生产率不断提高。而这使人们通过标志性商品获得上层社会的意义,反而变得只具有相对性了。经常地供应新的、时髦得令人垂涎的商品,或者下层群体僭用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便产生了一种‘犬兔’越野追逐式的游戏。”⑤城市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它造成了现代人的同质化。文化一旦进入市场,就必须服从市场的规律,无论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以利润为目的,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的文化工业,以高科技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介,以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娱乐为特征,把知识、信息、艺术、观念等流水线地复制出来并向全球传播,它在传播类文化的同时又扭曲了文化的类本质。⑥大批量的生产,大批量的传播,大批量的消费,文化艺术品越来越表现出形式和内容的趋同,标准化、数量化、模式化和单一性的非个性化颠覆了文化艺术的唯一性、创造性及自由个性。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形象地指出:“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系统是独立的,但所有领域又是相互联系的。甚至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的美学活动也都同样地颂扬铁的韵律。”⑦同质化的大众文化只能造就丧失个性特征的“单向度”的人,它是现代城市人“物化”的精神催化器。城市文化还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文化,它导致了人的文化认同的冷漠化、淡化。资本摧毁了传统的血缘关系,使利益关系成为交往活动中的唯一关系,资本的不安宁造成了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动,从而造成了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消解不断分化,人们在城市中普遍感到陌生、孤独和无助。“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⑧人的文化本质是在杂多流动的现象世界中追求终极关怀,在有限暂短的生命之旅中发现永恒价值,而当周围的一切包括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素被敬畏的良心和道义都被无情地亵渎的时候,当人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内容和形式都不停息地旋转而变得如此陌生的时候,处于这种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不可能拥有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批判不是目的,我们的使命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在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方面,斯宾格勒与马克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斯宾格勒对城市文化的没落的描写和分析在许多方面更为具体和生动。他认为城市统治的阶段——“文明阶段”是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但却是走向死亡的开始。世界城市的形成标志着文化发展到最高也是最终的阶段。“世界城市意味着世界主义代替了‘家’,冷酷的‘事所当然’代替了对于传统与时代的尊敬,科学的非宗教变成了古老的、精神宗教的僵死代表”,⑨城市窒息了人们的创造个性,也消解了人们的精神理想。“城市在经济史中属于首位并控制了经济史,以不同于物品的金钱的绝对观念代替了和农村生活、思想永远分不开的土地的原始价值。”⑩“从此以后,任何远大的生活理想就大部分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⑪更骇人听闻的是由于城市对传统、血统、家族观念的抛弃,导致性、家庭与生育相分离,“当存在失去根柢,醒觉的存在充分地紧张起来的时候,一种现象突然在历史的光辉中出现了,这种现象早已秘密酝酿成熟,现在出来结束这出戏剧——这就是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⑫这一切都决定了人类文化必然要在西方文明的阶段走向终结,回到无历史的自然状态。这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周期”。而马克思的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把城市文明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无情地批判城市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同时充分肯定工业和城市发展对于创造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交往条件的历史意义,并深入分析造成人的“异化”状态的根源,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从而揭示了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也为我们今天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大力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文化,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抗争和矛盾指出了方向。
从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建设城市文化。文化是交往的产物,一定的交往形式决定着一定
文化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⑬如同法律等上层建筑一样,文化不能从国家或从它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要从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来理解,也就是从“市民社会”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把它看作是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工业生活和商业生活,也包括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个变动着的历史范畴。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发展,从现代国家批判的角度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压迫,称市民社会为“私人自治领域”,或者叫“非政治领域”,强调城市和社区文化的个体性、自由性和平等性。我们要在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多样文化竞相发展的良性文化生态环境,激发每个人的文化个性,促进市民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回归,让城市化运动始终不偏离人的价值目标,让城市真正成为人的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
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出发建设城市文化。经济的全球化推动着文化的全球化。如果说,资本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那么,文化全球化也不可避免服从于资本和市场的共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必须纳入世界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的经济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同质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打破民族、地域的狭隘性,在与他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往中实现兼容式发展,是任何民族、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抹杀文化的特殊性的文化全球化只能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而离开文化普遍性的文化特殊性只能是游离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偶然现象。城市化与全球化实质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任何城市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和魅力,就要保持文化的民族和地域个性,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文化产业和文化环境。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厚实土壤上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本。
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出发建设城市文化。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区域和城市之间的竞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因素正在起变化,从以资本、管理、科技竞争力为主导到以文化竞争力为主导,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竞争力亦即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力,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人的感召力。在观念层面上,文化竞争力表现为是否适应人的价值追求,解放人的思想,提升人的能力,激发人的意志和理想。在实践的层面上,文化竞争力表现为文化生产力、文化消费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持续力等等。归结起来,有竞争力的城市文化或文化城市必须以文明进步的文化精神为灵魂,以先进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基础,以优秀的文化人才为根本,以法治的文化制度为载体。文化精神是城市人认同的纽带和创新的动力,是城市相互区别的文化标志,缺乏精神的城市是死寂的城市;文化产业不仅是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性产业,而且已成为新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人是城市的文化资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文化人才的流动和积聚往往反映一个城市的兴衰;文化制度是人的文化活动的政治安排,制度的合理性关系到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的活力程度。文化竞争力并不仅仅是这几种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以这几种要素为基础的行政的、社会的、环境的各种因素构成的有机的、开放的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运动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推动下蓬勃发展,以京津唐地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面城市化的新时代。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及人们文化需求的高涨,城市文化问题已日益凸现出来。如何从批判和建构、普遍与特殊、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进行学理探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以预期,在民族文化积淀深厚的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必将掀起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