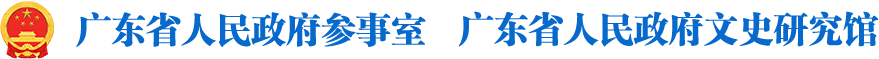
东汉末年,士燮兄弟以交趾郡为中心,领辖岭南七郡,交趾名重一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建安十五年(210年)交州治所移治番禺,黄武五年(226年),初置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番禺,而交州移治龙编(今越南河内附近),仅辖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地位远不及广州。虽广州旋废,但交州治所又移番禺,番禺始终为岭南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永安七年(264年)分交州再置广州,治所仍在番禺,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交州移治龙编,交广分治从此成为定制。随着政治中心向东南迁徙,六朝定都于建康(业),广州治所番禺距建康较近,北上逾大庾岭沿赣江入长江即达建康,而交趾、苍梧偏于西南,到达建康不如番禺迅捷。这些条件使番禺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广州治所番禺政治地位的重要。吴国末期郭马政变、东晋初年的王机叛乱等政治事变都发生在番禺,南朝卢循、陈霸先等都是以广州治所番禺为根据地而后北上的。随着大庾岭道逐渐成为3~6世纪越过南岭的主要通道,岭南主要通道的东移,加上时江左人南下和军事上的需要,“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 ,粤东沿海道也逐渐兴盛。卢循起义军和东晋沈季高、沈田之的军队等都是从粤东沿海南下番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的便利,为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样,魏晋南朝时,广州成为南海丝路的重要始发港。广州居三江之汇,北江、西江、东江交通方便,粤东海路也可达江左,故沿江和沿海多南迁之民,而居于三江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低平,土壤肥美,无疑成为南迁人口的聚居中心。随着岭南政治中心和交广两州的分置,加上广州政治清明,少战事侵扰,社会安定,因此,广州治所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都会。
南方其他对外贸易港口的衰落,也为广州成为对外贸易港口提供了条件。而魏晋南朝,随着海舶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原来的近岸航行可以取道海南岛东岸和南岸直达广州,上述的“重楼”“八槽舰”应是使用于海上航行,而域外的扶南国也“乃制作大船,穷涨海” 。据《南州异物志》载,“外域人名舡曰舡(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外缴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也” 。这些船体较大,随风调整帆数和帆向,为深海远航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和康泰《扶南传》都记载了涨海(今南海)有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 ;“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缴人乘大舶,皆以铁鐷鐷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 。盘石和磁石皆为今南沙、西沙群岛的暗礁和珊瑚礁。无论是作者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吴时已有远航船舶经过南海航行。不过,这时番禺还不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至少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其作为对外贸易之地。
三国时期,南海丝路的发展与吴国大力发展航海密切相关。黄龙二年(230年),孙吴大将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进驻夷洲(今台湾)。赤乌五年(242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珠崖(治今海南琼山东南,汉时辖海南岛东北部)、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辖今海南岛西部地区)为汉武帝时所置两郡,辖地当今海南岛,附近已是南海海域。海南岛纳入吴国版图,为南海丝路向东迁移提供了便利。不过,由于岭南中心城市广州番禺城在东吴初年兴起的时间不长,交州仍然在中外交通史上起着一定作用。
黄武五年(226年),吕岱平定交趾太守士燮之子士徽叛乱,“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 。这些东南亚国家应是沿近海达交州,从交州而北上至建业。同年,“其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 。大秦商人秦论怎样到达交趾?史书仅言“其国(大秦)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其(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 。则大秦商人应在中天竺、安息往来,向东还到达泰国湾以及南海,与扶南、吴日南郡、交趾往来,这其间沿近海航行的道路已从印度洋至太平洋,南海航路也向西扩展至安息、大秦境。
据《梁书 ·海南诸国传序》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朱应、康泰南洋之行是否就是吕岱所遣从事,史书简略,未敢妄断。继三国吴在南海上航行最远和影响较大的便是朱应、康泰的这次南洋之行。朱应所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所撰《吴时外国传》(也作《扶南记》《扶南传》《扶南土俗》《吴时外国志》)对这次航海和所见所闻记载详尽,可惜全佚。今仅从《水经注》《通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史书散见部分段句,可窥当时吴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的往来情形。
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国,应至其国及附近国家,地域当不超过今东南亚。因为康泰等在扶南见到天竺王派出回访扶南王的使者陈宋,“具问天竺土俗” 。据冯承钧先生考证:“传中所言非历之地,天竺、大秦,甚至加那调洲(当今缅甸沿岸),皆传闻之地也。” 时朱应、康泰等人应是从吴最南边境日南郡(或相近的九真交趾郡)出发,从陆上或海上向南达林邑(治今越南维川县南茶荞),从这里南下扶南。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从日南发往扶南诸口,常从此口出也。”扶南之外还有林杨国(地当今泰国西南部或缅甸东面部)、金邻国(地当今泰国境)、嘾杨(或作林杨,地当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说为苏门答腊岛)、无论国(缅甸卑谬一带,或为泰国武里南府,乌隆府)、优钹(今缅甸南部,或为孟加拉国)、典逝(北来半岛北部,一说为顷甸东南岸丹那沙林)、滨那专(地不详,在中南半岛)、蒲罗中(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一带,另有泰国北大年或万伦湾等说)、都有昆(在马来半岛,有吉打、瓜拉龙运、柔佛等说)、拘利(又作句稚,在马来半岛西岸帕克强河口,一说马来半岛南半东岸)、耽兰洲(今马来半岛东岸哥打巴鲁)、巨延洲(今加里曼丹,或谓今沙捞越的卡扬河)、北攎洲(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邦加岛)、薄欢洲(今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宾坦岛,另有人认为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或马来关岛)、马五洲(今印度尼西亚境,一说为巴厘岛)、火洲(今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岛一带火山)、诸薄(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毗骞(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一说马来半岛,另有印度南部)、加营(又作歌营,指苏门答腊岛,另有印度南部、马来半岛南部等说)、加陈(当今苏门答腊岛或印度西海岸)、姑奴(地不详,或谓在印度)、模趺(又作横向联合跌,今印度恒河口一带,另有缅甸沿岸、马来半岛南部等说)、乌文(印度东岸的奥里萨,另有安达曼群岛、马来半岛等说)、担衭(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之塔姆卢克)、加那调国、扈利国(或作枝扈黎、扈枝黎,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河口一带)、师汉(今马来半岛以西、直苏门答腊岛北部、印度东南岸、斯里兰卡等)、斯高洲(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安息、大秦等。“吴时扶南王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中天竺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 同样,据康秦《扶南传》,“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 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两者皆从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帕克强河口附近出发,向西北方向驶入孟加拉湾,到达恒河口。“从加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经西行极大秦也”,从缅甸沿岸至枝扈黎口(即恒河口),由此西行至大秦。
明确记载广州成为海上丝路的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坐镇番禺,“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 。虽然“晋代通中国者鲜,故不载史官” ,但广州(即番禺)外贸港的声誉已远播域外。法显从海上归国,在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东部,一言爪哇岛)“东北行,趋广州”。来往于此途的“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 。人们已可利用信风,准确掌握航行时日。这比《汉书·地理志》所载沿近岸航行要迅捷。刘宋元嘉七年(430年)诃罗陁国(今爪哇岛)“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 ,要求保护其国外贸船只。虽然这一时期有侵夺事件发生,但丝毫也不影响番禺“商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事 ,宋末,扶南国等“遣商货至广州”,至齐时,“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轫积王府” 。梁时,番禺“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 。萧劢为广州刺史时,变“每年(外)舶至不过三数”为“岁十余至” 。考古人员也在西沙群岛的北礁,打捞出南朝六耳罐、陶杯等遗物,这足以证明南朝时南海丝路确实已东移至海南岛东和西沙群岛附近。 南海丝路的东移,为广州(番禺)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宋时,中国航海在北印度洋方面也取得突破,开辟了由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锭洋船路,沟通了东亚与西亚的联系,正如《宋书·夷蛮传》所言:“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使),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古代阿拉伯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马苏弟(一译作马斯欧迪)也在其撰写的《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一书中提到,5世纪上半期,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的希拉城(时为希拉国国都,希拉国统治时期为3~7世纪初)常有人看到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中国帆船到达波斯湾头后,“中国和印度船只潮流而上去见希拉王”,中国的船只已远达阿拉伯国家。
宋末齐时,扶南等国仍以广州为对外贸易口岸。梁时,林邑曾九次派使节入梁,扶南也曾八次遣使入梁。东南亚的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半岛吉兰丹)、干拖利(今马来半岛吉打)、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等国也遣使节频繁往来梁廷。天监初年(502年)和大通元年(527年),中天竺国和狮子国也分别遣使与梁朝往来。 这些国家的许多僧侣也多乘大海船,由南亚而至中国南方,西天竺名僧拘那陀罗就是在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而至广州的。古希腊旅行家科斯麻士曾到过波斯、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并著有《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一书,书中对中国与东罗马帝国海上交通有所阐述:“产丝国(指中国,即下文的秦尼策国)在印度诸邦中为最远者。当进入印度洋时,其国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即东北方),唯离波斯湾及赛莱底巴(指锡兰岛)甚远。……产丝国之名为秦尼策国,大洋海环其左,此洋与环巴巴利(非洲东岸之地)同一洋(印度洋)也……若由波斯而经海道往彼,所需时日实甚久也。盖第一原因,航海者须由塔勃罗贝恩(希腊人对锡兰岛之称谓)所处之纬度及稍北诸地,船行长程一节,约有波斯湾之长,始得达其目的地也;第二原因,则渡过印度洋全境,由波斯湾至塔勃罗贝恩,曾由塔勃罗贝恩面转舵向左,以往秦尼策之地,海程甚远也。”
总之,正是南海丝路移至广州,广州才成为六朝时期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继徐闻、合浦、交趾等港口之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南海丝路的始发港。而且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原来沿近海航行的海上丝路逐渐东移,从广州经海南岛东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一线而穿越南海航行,到达加里曼丹、中南半岛南部、苏门答腊等岛屿,由马来半岛向西,经苏门答腊岛南北皆可入印度洋,经尼科巴群岛而西达斯里兰卡岛,由此向西北可达印度,向西可达阿拉伯海、波斯湾。正如阿拉伯人行记所言那样,“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六朝时期广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在整个海上丝路的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为唐代市舶使的设置以至最终确立广州在全国对外贸易最大港口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广州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